任继周:青青寸草,悠悠我心
“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
而是戈壁风、大漠道,
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
98岁高龄的任继周犹记得那个美梦。
那是2009年5月,住院整20天的时候。晨昏恍惚之际,院外的车流声,恍如忽紧忽慢、忽轻忽重、若断若续的风雨声,如天籁般,把他从枯寂的病房带回广阔的草原,抛入了静卧在草原风雨中的帐篷里……
草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扎根草原70余年,他总自称“草人”,夫人李慧敏曾笑称,“他这一生全为了他的草,脑子里也像长满了草!”
如今任老已近期颐之年,人生如草原般浩瀚,学术“草原”亦百草丰茂。但他依然如一株青草,葆有纯净、坚毅和旺盛的生命力,兀自生长。
人生的“序”
“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许多倍于株高的地方。”
——任继周《土地深层的乐章》
出生在战争年代,12岁的任继周便离开家乡平原,在鲁鄂川渝等多地求学辗转。
任继周弟兄四个,大哥早逝,二哥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三哥是经济学家任继亮,任继周最小。年长8岁的二哥任继愈“亦兄亦父,亦师亦友”,如天边的星辰,始终为他领航。
随着年龄的变化,任继周一生有两个座右铭,一直被他奉为圭臬,而这两个座右铭都是来自任继愈。
第一个座右铭来自他的中学阶段,一直陪伴着他到71岁。
任继愈认为,中学阶段是养成人格品质最要紧的阶段,因此一入初中,便给弟弟任继周制订了“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领先,分秒必争”的座右铭,鼓励他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并要求他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小草柔弱,但它的根却可以扎得很深很深,而读书就是青年任继周最专注的事。“我对每一个生活阶段都订立学习计划,计划可包括多项工作,但其中必须包含读书。”任继周说。
初二下学期转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时,体弱的任继周患上了细菌性痢疾,当时缺少药物,痢疾不时发作,只能长期卧床。于是,四书五经、英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把学校三间阅览室的书全看完了,并且学业成绩出色。
“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没!”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任继愈得知弟弟的情况后,给父亲写信道,并决定省吃俭用,送弟弟到当时大后方最知名的私立学校——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缴费的时候吓我一跳,一年的学费相当于我哥哥10个月的工资。当时我就下决心,只交这一次,第二年我就要考大学。”任继周信誓旦旦。于是,更加拼命读书,一边学习高二课程,一边自学高三课程,次年如愿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
选择什么专业呢?“我研究哲学有些务虚,你最好选实一点的专业。”任继愈建议。当时的任继周骨瘦如柴,第一志愿就报了当时的冷门专业——畜牧业。
面试时,院长冯泽芳院士好奇地问他,你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业?“我的身体不好,不光我,中国人的身体都差,又瘦又弱。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我愿意用自己的所学,让国人强壮起来!”任继周说完,只记得冯院长含笑道,“你这口气不小!”
中央大学一年级设在很偏僻的嘉陵江边,旁边都是乡下橘子园。任继周如饥似渴,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览室。早上一开门,他冲进去先把靠近英文《韦氏大词典》的座位占住,然后四处去找书。一年过去了,任继周阅读英文的速度已经跟中文无异。而用来填写借阅书目的“借书证”,他一年换了三本,是一般大学生的两三倍。
这段时间,日记一直伴他度过。“那连日连夜的车船拥挤,崇山峻岭间疲劳的长途跋涉,难民学校里的寒冷、饥饿,嘉陵江边的病困孤独,居然保持了精神的基本健康,收获了一些人生的厚重。这多亏二哥继愈教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任继周在文章中回忆,“日记像是精神的胃肠,生活的杂质在这里分选、吸纳和扬弃,它滋养着我熬过重重苦难,走到今天。”
1948年正式毕业,时任国立兽医学院(兰州)院长盛彤笙教授托王栋找一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赴兰州之前,学校安排他毕业后以助教的身份,跟随王栋进修两年牧草学。
这段时间对任继周来说可遇不可求。当时汤逸人先生辞掉联合国粮食组织顾问的职务,将所有积蓄都买成了书从海路运回,两大木箱书大概三四吨重。任继周去代为开箱清点,逐一打字造册。
“这些资料有关家畜管理的、动物营养学的、遗传育种的,乃至农业的、环境的书籍大大小小,厚的薄的,种类繁多。”任继周一边做目录,一边看书,兴奋到昼夜不停。尤其是1948年美国农业年鉴Grasses和新版的大学教科书RangeManagement(《草原管理学》),让他对世界草原状况和最新的科学成就了然于胸。
“我相信,当时我掌握的草原方面的材料是国内最多、最先进的!”任继周说。生于平原的这株小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准备奔赴最适合他的草原。
立草为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恩师王栋送给任继周的对联
1950年,一辆载着任继周及家人的美式旧卡车,行驶在蜿蜒崎岖的碎石路上。在飞扬的黄土中,破旧的车一再抛锚,他们从西安出发,在路上颠簸了21天才到兰州,自此开启了他扎根西北70多年的人生。

1950年初,任继周在兰州鉴定牧草标本。
初到西北,迎接他的就是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实验室,里面却什么实验设备也没有,“台灯都是摆样子的,不怎么亮。”任继周回忆道,只记得每晚在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然而,他对物质条件的恶劣和匮乏毫不在意,因为他被巨大的兴奋笼罩着,“学校的实验室虽然简单,但我有大自然这个大实验室,是没法取代的。这是研究草原科学的圣地!”
“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甘肃呈哑铃型斜置中国西北,任继周爱屋及乌,称它为“玉如意形”。
5月到达兰州,6月,他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外出考察。
野外考察中,马车是最好的工具,方便随时采集标本。但有的时候是骑毛驴,“驴子跟马不一样,它不走中间,溜路边走,要么这边是山,山岩磨你的腿和行李;要么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让人心惊胆战。”回忆起来,任继周仍心有余悸。
然而,最大的困扰是虱子。“不管坐在老乡炕上还是骑马的时候,虱子都会源源不断地从垫子上钻进你的内衣,叮咬得你坐卧不宁。”为保住一个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他特制了一件上下衣相连的工作服,每一次到野外都用“六六六”等农药浸泡衣服,晒干后直接穿上,下乡时昼夜不脱,这才治住了蚊虫。“那段时间,我身上几乎试过每种新农药。现在身上应该是百毒不侵了吧。”他乐观地说。
就这样,他以每年跑烂一双翻毛皮靴的速度,走遍了甘肃和宁夏(那时宁夏属于甘肃省银川地区)的草原和牧区,对全省草原状况进行了初步考察。
然而,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1954年,在海拔3000米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草原的马营沟上立起两顶白色帐篷,任继周的临时驻所与做定点观测的实验室就这样落成了。
草地灌丛杂生,人迹罕至,狼、熊经常出没,并且单层帆布帐篷避风不避寒,早上做饭柴湿烟浓而无火,狼狈万状。“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迹绕帐房。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任继周曾用诗生动地记载当年状况。
就这样度过了两年,1956年沟里头盖了几间房子,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甘肃天祝草原站,在全国率先开展高寒草地改良研究。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学,后4天到试验站工作。即便如此,他的教学工作也从未耽搁。他是公认的优秀教师,“每讲两节课,我备课至少8小时”,甚至在奉命援越的离校期间,也高票当选全校唯一一名甘肃省劳动模范。

1958年,任继周(右1)在越南农村考察。
“每样工作我都认为是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锻炼机会,不管多么累,我都力求‘最好’。”总是“计划领先”的任继周,在草原上留下了多个“第一”:
20世纪50年代末,他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是国际上第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类系统;1973年,任继周带领的学术集体还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使当地草原生产能力提高5倍,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
他的学术“草原”亦不断生长。195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1959年出版的《草原学》教材是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1964年,倡导创办了草原专业,后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1977年,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草原。
在甘肃的前30年,任继周说像是在梦幻中度过,醉梦般享受着美好,也醉梦般忍受着磨难。但是,“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一直坚持建设草原站。”他的心境光明澄澈,向往光明的浪漫情怀从未衰减。
为草正名
千曲黄河穿荒沙,忽现沃野望无涯。麦黄豆绿苜蓿蓝,胡风汉雨开新花。
——任继周《河套沃野》
上世纪70年代,任继周心痛地见证了过度开垦导致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不断溃败,“先是草类产量下降,接着是品质变坏,殃及生活在这里的家畜,最终影响到牧民的生计。”
“草原不仅是草原,是草业的问题。”任继周对照过去所见、所思,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视野大开。他认为这一切根源在于“以粮为纲”的压力下,草原牧区与农耕地区截然分割导致的生态系统缺失,并希冀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胡风汉雨”下早日新花绽放。
很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春天来了。
“‘以粮为纲’下的耕地农业是瘸腿农业,光吃五谷杂粮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强壮的强国国民的,草地农业正好可以补救耕地农业之不足。”立志要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结构,年近花甲的任继周不得不日夜兼程。
1979年,任继周在甘肃农大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开始草业的教学和研究。1981年,任继周拿着10万元经费、带着10个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新征途,创办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以期打破我国农牧业分割的格局。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将其建设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草原科学重点学科点。

1981年,任继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中国草原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然而,触及当时“以粮为纲”的国策,草地农业的理论和观点一时很难被人接受。正苦于迈不出校园,恰逢钱学森先生从战略高度倡导发展“草产业”。
“我数了数,林业有16个产业部门,草业有多少产业部门?”1985年6月24日,北京民族饭店,任继周第一次与钱老见面。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草业,钱老这一富含战略深度的提问,启发了任继周对草业做结构性思考,一年后形成了三个因子群、三个界面、四个生产层的草业科学框架雏形。
1998年国家大幅度调整学科系统,专业门类大量裁并,草原科学不但没有被删除,反而由草原科学提升了一级,成为与农、林、牧并列的草业科学。从草原到草业,一字之差,却将草地纳入到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填补了中国草业科学的空白。
草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理论开始走向社会实践,但社会文化中仍对草充满不敬甚至敌意。
“草包、草寇、草草了事、草菅人命,都表现了对草的贬义。”任继周多次为草鸣不平,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传统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厌草”情结。反之,他欣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美了草顽强坚毅的勇士品格,是为草翻案的千古绝唱。
而他一如闯险犯难的勇士,始终坚持为草业正名,为农业结构改革奔走呼号,从未稍歇。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动物性食品在食物中的比重明显上升,饲料、牧草的不足给我们的粮食安全带来隐忧。耄耋之年的任继周更觉时间紧迫,不断向外界呼吁——建立新的食物系统观,以草地农业系统确保粮食安全。
这一阶段的所思所想所悟,很多被他写成文章,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草业琐谈》里。张子仪院士在跋中称:“《琐谈》借助于大量纪人纪事纪言为‘草’纠偏,为‘草’正名,为‘草’寻根,是一部为‘草’平反的号角。”
“草人携囊走荒谷,带泥足迹没丛芜。”任继周常用“草人”自称,作为一个草原工作者,他不断在草业科学中跋涉,盼望着草地农业不再是寂寞无闻的“荒谷”,能真正被社会所认可。“丛芜兴而足迹灭,正是我草人的夙愿。”任继周说。
终于,草业系统尖角初露。“2015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出台,已经从正面回答了我对农业结构改革的论述。”任继周欣慰不已,草地农业是生态安全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相信“牧草比肩看稻粮,畜群如云接天外”的盛景将不日重现。
70余年扎根草原,任继周经历过太多诱惑。但不管是美国高校的邀请,还是“东南飞”的邀约,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而是戈壁风、大漠道,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他觉得在这里,自己的专业与志趣融为一体,工作与生存融为一体,自我与环境融为一体,获得的是生命的净化、充实和乐趣。
正如他念念不忘的恩师——盛彤笙。1936年取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却数次“倒行逆施”,不仅改攻兽医,还西行到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虽然历经挫折,但他发展畜牧、改善国民食物构成的志向终生不渝。
“盛老对我的人格教育太深刻了。他的未竟之志,我要坚持下去!”任继周感言。
生生不息
渐多足音响空谷,沁人陈酿溢深潭。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竿复三竿。
——任继周《从业七十周年有感》
1995年,任继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当时他感受更多的是沉郁,更希望这份“高光”属于他心爱的草原。

任继周在贵州扶贫考察。
“虽然草业科学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进展缓慢,我们的学术核心思想——草地农业系统远未取得社会充分理解,该系统的落实更渺茫难期。”献身草原近半个世纪,任继周觉得自己承受着时代的谴责。
“检查自己,既‘空’又‘松’,几乎走上了学术的死胡同。”任继周常以华罗庚先生“树老忌空,人老忌松”的名言自省,同时不忘勉励自己,“感恩时代赐予的宽恕与困厄,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跨越学术低潮。”
在纷乱复杂的心境中,二哥任继愈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生高低行止,勉励他做好“涵养”功夫,保持心境的澄澈、平静,坚定地走选定的路。
任继周把它作为人生中第二个座右铭,从71岁坚持至今,还给自己的居所也取名为“涵虚草舍”。
这句话成为他晚年的定海神针。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80岁的他对孔子人生的“序”做了修正,“八十而长存虔敬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拾贝,得失不计,融入社会而怡然自得;九十而外纳清新,内排冗余,含英咀华,简练人生。”
进入耄耋之年,他已无力躬亲参与农业结构改革的实际操作,反而转向多年压在心头的问题做深度思考。中国耕地问题的源头何在?为什么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冒出个三农问题?于是他从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发展历史起步,逐渐进入农业伦理学思考。
“伦理学是很深厚的一门学科,要慎重一些,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任继周回忆起他二哥对他的提醒,但他还是要坚持往前跨一步,完成“草人”的使命。
他认为,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必须要在伦理上论证农业的发展方向,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晚照斜晖无限好,这株“草”好像有着无尽的生命力。
在鲐背之年,主编并出版了《中国草业系统发展史》《中国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等专著和教材,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
如今,虽已近百岁高龄,但他身体依然硬朗,面对着一张大投影屏,每日坚持工作6个小时,继续在莽莽草业科学世界中徜徉与跋涉。
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去,但他已经能平静接受生命和时代的赐予。他说,“人活着的意义要有益于人,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死则是自然规律,是另一种活着,当坦然视之。”
花开花落自有时,而他心中的草原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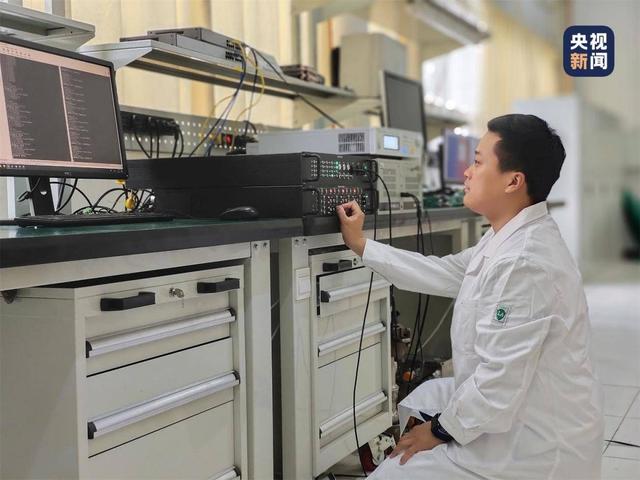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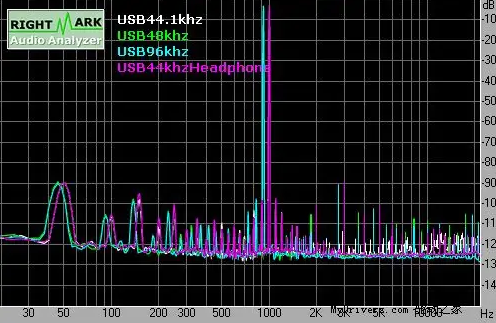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