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里两次停摆的音乐剧演员,正在等待上海“解冻”
赵嘉艳坐在电脑前,屏幕那头是她的搭档。一段台词说完,轮到对方了。而对方刚说到一半,赵嘉艳就抢着说出了下一句台词——按照剧本,她本该在男主话音未落的时候抢话,但视频会议有延迟,她只能预判搭档的节奏,还没到抢话的点,就把话抛出去——这样一来,男演员能及时听到她的反应,戏也能自然地顺下去。
赵嘉艳是音乐剧演员。联系上她时,她所在的《浮生六记》剧组已经恢复排练——但是是在线上。
这让她很不适应:除了要“预判”对手的反应,网络延迟带来的沉默和犹豫也总让她无法入戏。在她的认知里,演员不是程式化的工作,是灵活的、需要打开感官去应对。演员们很忌讳在表演中“预判”搭档的反应,因为这不专业。而为了线上排练的质量,赵嘉艳笑称,自己已经“打破了作为一个合格演员的标准”。
6月1日起,上海各项秩序逐渐恢复。静默两个月后终于等到这一天,赵嘉艳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激动。这天凌晨她失眠了。中午醒来的时候,她发现所在社区的疫情防控群、党员志愿者微信群,都被居委会解散了。她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封控期间,赵嘉艳在社区里做团购志愿者,帮邻居团菜、分发,那是她过去两个月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而那时,她觉得大家不论年龄、职业和性别,面临的处境都是一样的。现在解封了,邻居们回去上班、恢复正常社交,在她看来,其他人找回了自己原本的自我价值,而她好像停在了一个真空地带。

封控期间,赵嘉艳在社区做志愿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非必要”的演出行业,音乐剧需要慢慢“解冻”。而整整一个季度的停摆给行业带来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恢复。
延期、延期、延期
赵嘉艳的工作是在3月中旬停下来的,但到现在,她还没收到线下复排的通知。她觉得,尽管《浮生六记》进度还不错,但已经达到了线上排练的极限,再练下去也没什么意义。经过这两个多月,她相信任何制作公司在此时都会选择小心行事,“毕竟要面对面排练,要等到大家都能安全、安心地聚集时才行。”
在赵嘉艳原本的计划里,这个春天她应该是极其忙碌的:三四月份紧锣密鼓地排练,两部以她为女主的戏将轮番上演;五月趁休息去旅游;六月复排一部曾经出演过的戏。因为去年的剧目全都在春节前收官,她计划着在今年上半年好好琢磨角色、全新出发。
如果没有疫情,这座城市每个月会有近80场音乐剧演出。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每个寻常的夜晚,人们从办公楼里、家里出来,汇聚到全城的几十家剧院里;公交地铁的电视里循环播放着近期大火的音乐剧演员访谈;邻近剧院的地铁站墙上挂着一排排的音乐剧海报;开场前的餐厅里,剧迷们背着剧目周边的同款包,餐桌间讨论的都是演出;两三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人们走出剧场,兴奋的谈论声随着车流散去。第二天,周而复始。

2019年,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上海。程靖/摄
许多人说,有音乐剧看的生活是他们“喜欢上海的理由”。在外地观众口中,每逢新的音乐剧上演,中国就只剩下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那是羡慕的调侃,因为这座城市聚集了为数众多的音乐剧制作公司、演员和观众,剧目通常先在这座城市诞生、被看到,然后才能有限度地“走出去”。
5月下旬,赵嘉艳得知自己原本6月要复排的戏也被延期。这意味着整个2022上半年,她没有上台演过一场戏。
美声出身的演员殷浩伦去年刚进音乐剧圈。常驻北京的他3月下旬来到上海,才进组排练了4天,就被叫停。
4月初,剧组改为线上排练,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箱子、雨伞等道具都放在排练厅,家里也没有T型舞台。至于在家里练习走位的体验,殷浩伦直言,“还挺蒙的”。
更要命的是,戏中的舞蹈多是双人舞,但在视频会议里,编舞老师每次一个人展示两人的舞蹈动作,只能对着空气搭一下肩、扶一下腰,都像是“无实物表演”;再加上视频是镜像的,殷浩伦总是得反应一会儿,“这是左手,还是右手?”
如果顺利,殷浩伦的戏应该在5月上旬合成、下旬上演。6月初,他收到通知,6月6号要恢复排练了。但他很快又得知,排练厅附近在排查密接者,排练又要延迟一周。
“有没有人想听我唱歌呀”
“有没有人想听我唱歌呀?”在家憋了一段时间后的一个下午,李炜铃打开窗户,对着窗外喊——她想好了,假如邻居们回答了她,她一定要问问他们想听什么歌,她给他们唱。
但窗外无人回应。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李炜铃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女演员之一,参演的几乎都是大制作中的女主角:《猫》里的天真猫、《狮子王》里的娜娜、《人间失格》里的女主角祝子。今年她还参演了东方卫视的音乐剧综艺《爱乐之都》。

李炜铃在《人间失格》中饰演祝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李炜铃来说,封控的日子不算太闲。她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音乐剧系的老师——即使不排练、不演出,也要上网课、准备期末考。她主演的《人间失格》原本计划在3月下旬开启全国巡演,但因为疫情延期。封控后,她甚至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4月16日,她原本要在陕西大剧院献唱一场迪士尼经典曲目的音乐会。演出推迟后,这个日子在记忆里就不再特别了。被问到那天在做什么时,她拿起手机翻了翻朋友圈,才想起那天在家烤了一个熔岩蛋糕。她在微博上给粉丝分享了她的作品,粉丝们调侃说,蛋糕像“平底锅”、“照妖镜”。但她很满意,“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尝试自己做甜品。这蛋糕虽然卖相不好,但味道还不错。”

李炜铃做的熔岩蛋糕被粉丝说像“平底锅”和“照妖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炜铃来自厦门,海边炽烈的阳光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雀斑, “阳光对我来说就像氧气一样!不能出门骑车晒太阳,太难受了”。但在疫情管控、足不出户的这段日子,这位“厦门海娃”也时刻告诫自己,“要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4月8日是赵嘉艳入行7周年的纪念日——7年前的那个春天,她辞掉国企工作转行做了演员。她原本计划着和第一部戏的同事们一起直播聊天、唱歌,纪念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但这一天她是从早到晚盯着手机团菜度过的。封控的第一周是物资最困难的时候,她所在的小区又多居住着老年人,她自告奋勇帮楼里的邻居团购——但邻居找来的渠道物资是有限的,她得眼疾手快。一旦落后,大家就要饿肚子了。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赵嘉艳……啊不好意思,我们楼有人加2盒鸡蛋!马上截单了我先去登记一下稍等!”被买菜占据的纪念日快结束时,她“创作”了这个场景,发在自己的微博上。有剧情,有节奏感,她的粉丝说,这很“音乐剧”。
赵嘉艳的团购工作一直持续到了5月31日。
这两个月以来,她的生活大约是这样的:早上被社区的大喇叭喊下楼做核酸,回来缓一缓后做午饭;进入五月,下午偶尔参加线上排练,然后做晚饭;晚上和社区里的志愿者们聊聊天,或是看一部电影,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嘲道,如果不排练,一天的时间都得用来做饭、吃饭、做家务;还间歇帮楼里的邻居接龙买菜、分发物资,感觉自己的本职不再是音乐剧演员,而是在居委会上班。

封控期间,赵嘉艳和邻居们自发组成流水线,分发团购来的物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来上海,毫无准备的殷浩伦则一度陷入物资匮乏的境地。居家到20天时,他的出租屋里已经没有菜、没有肉,鸡蛋也快吃完了。4月21日是殷浩伦30岁的生日,原本不爱过生日的他,想在这一天制造出点儿仪式感——蛋糕,或者来碗生日面。但他连续好几天早起抢菜,都一无所获。
21日那天早晨,殷浩伦已经“躺平”,起床时已过了抢菜的时间。他拿起手机随便看了看,却意外地在生鲜APP上“捡漏”到了一只烧鸡和两瓶红酒,他相信那一定是生日给他带来的好运。那天晚上,他还用仅剩的几根青菜和鸡蛋给自己做了一碗生日面。

殷浩伦用仅剩的物资给自己做的生日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就好像看到剧场重新开花了一样”
对演出行业从业者来说,2022年的春天是他们第二次经历停摆了。殷浩伦也不例外。
2019年夏天,殷浩伦作为美声歌手参加了声乐综艺《声入人心》的第二季。节目结束后,他受邀参加巡演、录制和拍摄,全国各地飞,“经常晚上演出结束连夜就走,第二天还有工作”。但2020年春节前,疫情给他踩了急刹车——他回家过年,在家一躺就是五个月。
“之前那么忙,一下子就没了任何工作,每天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种心理落差太大了,差点调节不过来。”后来,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在还没有工作邀约时就回了北京,给自己找事情做,状态才慢慢好起来。
殷浩伦成长在音乐之家,妈妈是钢琴老师。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声乐歌剧专业。高中时期他看了《歌剧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音乐剧,想着自己喜欢唱歌、喜欢表演,也喜欢舞台,就找了老师学习音乐剧、准备艺考。“当时年纪小,憋着一股劲儿就想要换专业”。
但家人不赞同,希望他继续学习音乐,而不是表演。最后他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歌剧系。
声歌系的学制是五年。大三时,殷浩伦开始去歌剧院当群演,还带了两年艺考学生——对他和他的同学来说,哪怕来自金字塔尖的音乐院校,由于专业院团的演出机会太少,学音乐、当老师的“业内闭环”是一种常态。毕业后,殷浩伦给一些录音棚录制声乐小样,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那种“吃穿不愁”的稳定工作。
他的声歌系同学里,本科毕业后就转行的不在少数。直到毕业一年多后,他考进了母校组织的专业合唱团,才拥有了第一份全职工作。2019年参演《声入人心》是一个转机,但他的事业刚起步,又遇到了2020年初的疫情。
疫情的常态持续了两年多,“演出行业比较惨,很多工作一直在推迟。”殷浩伦后来意识到,“如果一个工作推迟个一年半载,到最后肯定就黄了。”2020年7月,他拥有了毕业以来除了节目巡演外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和男高音戴宸一起演出。现场演出仅允许三成上座率,但看到能开放的座位都坐满了,他特别开心。

殷浩伦在演出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艺考前那个辗转学习音乐剧的夏天,到去年进入人生第一部音乐剧的剧组,殷浩伦已经等待了整整11年。这一次再次按下暂停键,他心态稳了很多,“毕竟是第二次经历了,我又长了两岁。更何况,现在我有整整一本台词和歌曲可以学。”
李炜铃也是第二年给学生们上网课了。隔着屏幕上声乐课的时候,学生们都闭着麦,她看不到他们的脸。她会想念在琴房里和学生一起唱歌时,空气里的化学反应,“每当我讲解完一个要点,同学们恍然大悟,就开始‘哦’,然后大家一起叽叽喳喳地,在琴房里笑着唱着,很欢乐。”
2020年那次居家隔离,她没太焦虑,“因为当时真的觉得新冠病毒很可怕。先把病毒的事解决了,剧场的事可以慢慢来。”她认为自己算是幸运的,因为那时上海文化广场复工后上演的第一部戏《春之觉醒》,她就是女主角。
彼时的剧院只允许30%上座率,“疫情后第一次上台,观众席‘空荡荡的’。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大家虽然隔着几个座位坐,还戴着口罩,但30%的座位都坐满了。我相信观众都是因为特别热爱音乐剧才来的。”后来,李炜铃见证了剧场上座率恢复到50%、75%再到100%的过程,“就好像看到剧场重新开花了一样”。
“上一次疫情时,我知道只要不出门乱跑、做好消杀,就一定会等到一个好结果。”但这一次,赵嘉艳直言有些“创伤应激”。
戏的推迟让她感到失落和遗憾。《浮生六记》已经上演过,她是新的“芸娘”,这个她细细琢磨了很久的角色,原本应该在3月底亮相。但演出推迟后,她要和几位从未演过这部戏的演员一起见观众,“本来还想作为新人,让老演员带一带我。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循序渐进的踏实感。”

赵嘉艳的新角色“芸娘”原本要在3月底上演。
另一部她重度参与剧本、投入很多心血的新戏《斜杠进化论》也被延期。用她的话来说,延期对剧组打击尤其大,因为原创剧在首演前不仅要排练,还要创作,演员多、音乐复杂、投入大;整个上半年,大家都不能演戏,所有戏都要在下半年扎堆,剧组还要重新和剧院安排档期;演员们的时间安排也都乱了,部分演员不得不轧戏,甚至可能退出。
不演出意味着收入骤减。赵嘉艳说,国内音乐剧演员的排练收入和演出收入差距很大,每天的排练费仅有200-250元。疫情期间,这份收入还能算一笔“买菜补贴”,若不排练则连这笔收入都没有。而这行里不少演员是自由职业者,需要自己交社保、租房,如果没有积蓄的话,日子会比较艰难。
尽管最近已在线上复工,但她还是没有安全感:戏剧行业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现场演出,因此每一个剧组都要规划好排练和演出的时间比例。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让演出延期、取消;演出行业最早停摆、最晚复工,恢复起来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如果这一次也先恢复30%的上座率,哪一个剧组会允许自己亏本演出呢?”
“上海观众把台上的演员唱哭了”
对音乐剧不了解的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演员和剧迷们对它的热爱。
2002年6月,一架波音747飞机从旧金山飞抵上海,搭载着90吨重、造价超过400万美元的《悲惨世界》舞台道具。彼时这部在伦敦西区连续上演17年、在全球35个国家演出过4万多场的经典音乐剧,历经整整5年的谈判才成功落地上海。上海人、音乐剧迷满月记得,那是一件连电视新闻都报道了的大事。
直到很久以后,满月才知道自己当年错过了什么。她和剧迷交流时听说,那轮演出请到的“天字一号”“无可替代”的冉·阿让扮演者寇姆·威尔金森,是外方公司为了中国巡演的质量,自掏腰包用10万美金酬劳请到中国的,而同期进行的韩国巡演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满月说,当时最贵的一张票要680元,而那时一个上海普通职工的工资也就2000多元:“当年能看得起那部剧的,应该都至少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毕竟票价不便宜。而我就是当年那个零花钱不够,也没时间的高中生!”
那是国外原版音乐剧第一次在中国上演。2002年也因此被视作上海的音乐剧“元年”,上海音乐学院在这一年新成立了音乐戏剧系。此后的每一年,上海都有来自国外的原版音乐剧上演。上了大学的满月终于有了自由时间和零花钱,《狮子王》、《发胶星梦》、《歌舞青春》等百老汇音乐剧也成了她每年必看的娱乐。
但那时,在上海和少数剧迷之外,仍然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音乐剧。
2006年,厦门高中生李炜铃要参加艺考,偶然听到了上音音乐戏剧系在鼓浪屿的宣讲,才知道了“音乐剧”这种又唱又跳、还能表演的艺术形式。就在同一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音乐剧社团。赵嘉艳在5年后成为了这个社团的社长,但她在学校排练、演出之余总被问道:“你们在干什么?音乐剧是什么?是歌剧吗?”

赵嘉艳(右)在演出中。图/上海文化广场
从上外国贸专业毕业后,赵嘉艳进入了一家国企。但她放不下音乐剧梦,会在上班之余参加剧组面试。用她的话来说,2013年左右的音乐剧产业“还不景气”,“没什么机会,剧组看到非科班出身的简历,会直接刷掉”。所以,在面试成功,可以当音乐剧《Q大道》的“超级替补”时,她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辞掉了令人艳羡的稳定工作。她一度以为自己演完这部戏就会失业,最后还要回去上班,但这个行业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她也“幸运地”拿到了一个接一个的角色,一直演到了现在。
李炜铃从小就是迪士尼的死忠粉。2014年,得知即将落成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要为驻场音乐剧《狮子王》招募演员,她热血上涌——她爱这部戏,也热爱娜娜这个角色。当时她想的不是“我要去面试”,而是“我必须面上这个角色”。后来,经过5轮、历时3年的面试,她真的成为了“娜娜”,“演《狮子王》是我的梦想,最后我真的站在舞台上,成为了迪士尼乐园开园大戏的一分子——我想我这一生都会非常感谢这段经历。”
她一边做演员,一边带学生,“现在我能把我的实践经验教给学生,他们可以带着我的经验在舞台上实践,有时甚至能和我的学生同场竞技。这些都可以在上海这座城市实现。”

李炜铃给学生上网课时的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悲惨世界》的制作人麦金托什曾说,“音乐剧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观众,而不取决于我们。”
满月就是这样一位热爱音乐剧的观众。长大后,她一直想弥补高中时没看成《悲惨世界》的遗憾。当这部剧的法语版音乐会在2018年来上海时,在德国旅游的满月特意改签了机票,提前回上海看演出。那时她已经是骨灰级音乐剧迷,喜欢的剧可以连刷十几场——上海的剧迷们爱钻研,看演出的机会又多,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她最爱的《摇滚莫扎特》那年也在上海上演。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剧迷们冲到台前,跟着音乐大声合唱。大幕重新拉开,剧迷们拍着手、唱着歌、尖叫着为演员们喝彩,演员们则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来鞠躬、致谢。
最后,在剧迷们《纵情人生》的歌声中,主演米开朗琪罗·勒孔特干脆从舞台中央走上前,坐在台口,静静地听着。起初,其他演员们只是站在上台口的帷幕后拿着手机拍下这一幕,一曲听毕,也都纷纷走到台中央。和观众道别的时候,米开朗琪罗几次哽咽地说不出话。观众拍下的返场视频里,场上一位女演员拉起自己的裙摆擦眼泪。
那样的场面出现过许多次。同一年,在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末场谢幕后,剧迷们涌向前,舞台下、走廊里全部站满了人,大家自发地为演员唱歌。满月说,那次他们和剧院打好了招呼,后者用大屏幕打出了法语歌词。剧迷们的热情再一次把台上的演员唱哭了。
后来,该剧主演达米恩·萨格来上海开演唱会。剧迷们知道他一定会演唱《罗朱》中著名的对唱曲《爱》,但主办方却一直没有公布女嘉宾的名字。满月和朋友们猜测,“女嘉宾会不会是我们大家”?
演出那晚,达米恩真的把女声部分留给了剧迷们齐唱。“原来我们就是他的朱丽叶!”满月一下子感到,自己不再只是看客,而是真实存在在这个环境里的“主角”。而这就是音乐剧的感染力所在。
2021年,全国音乐剧行业演出1.53万场,票房10亿元,体量不及一部院线电影。但这其中是从业者们的生计和梦想,是无数剧迷们的快乐和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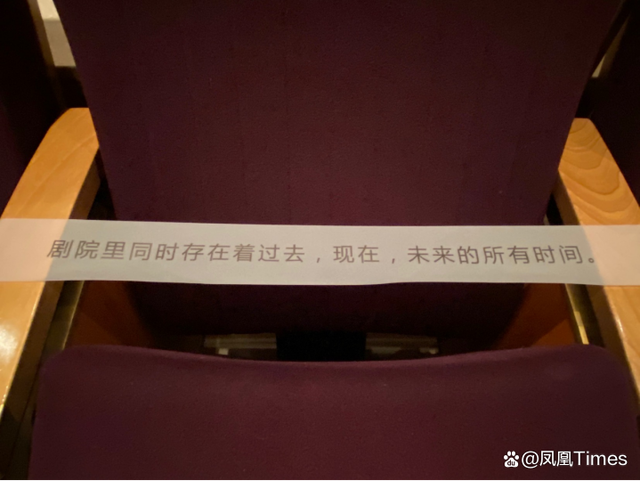
2020年5月29日,上海文化广场复演音乐会,观众席上贴的隔座封条。
2020年5月29日和30日,在剧院停摆127天后,上海文化广场剧院举办了两场复演音乐会。赵嘉艳、李炜铃和满月都去了现场。大幕一拉开,坐在台下的李炜铃就流泪了。
两年后的5月30日,满月在朋友圈里重发了那场演出的照片。
她感慨道,音乐剧是她一生的情感体验和寄托。她不知道下一次再走进剧场会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演员们也在等待下一次登台。上海的秩序逐渐恢复后,此前还未走出上海就被中断的《人间失格》巡演终于可以重启。李炜铃记得剧中的一个场景:寒冷的冬夜,舞台上下着雪,她开口的时候,漫天飞雪变成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剧里,她就像一个小精灵一样遇到了男主人公,她告诉他,黑暗中不仅仅有绝望,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正如那冬天里的萤火虫。
(满月为化名)
【版权说明】本文由百度“扬帆计划”合作媒体【凤凰Times】创作,独家发布在百度百家号,百度公司享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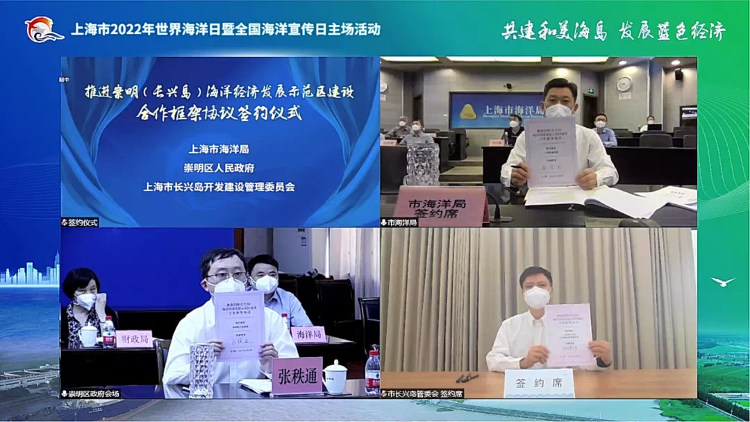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