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镜》:从“她”看见自己
刚刚公布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张莉获得了文学理论评论奖。张莉一直尝试在文学文本与公众的关切之间建立联结。
在花城出版社新出版的《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中,作者张莉从“自我、困境、关系”三个与女性切身相关的维度入手,从鲁迅、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冯骥才、铁凝、王安忆、苏童、毕飞宇、迟子建、东西等多位名家作品里挑选出二十多个典型的文学形象,以这些人物形象来映照当今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生存。
怎样做才是真正尊重女性?谁来定义女性美?何为女人的体面?怎样理解女性情谊和互相嫉妒?金钱能否真正衡量爱情?离婚就是被抛弃吗?母亲是否也会被孩子的期待绑架?……以文学为镜,解释当下。
8月26日,张莉、水木丁、季亚娅、柏邦妮也以此书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分享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图
谈起这本书写作的初衷,张莉说:“这些年来,我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越读就越认识到,文学研究者、文学教师的摆渡人角色,也就越来越希望能将那些美好的文学世界介绍给更年轻的读者。所以,很希望读者们通过这本书爱上那些作品,去重读本书中提到的作家。”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多困扰,所以《对镜》这部作品采用了问题的形式来建构,比如“女性在爱情中如何成为自己”“何为女人的体面”“母亲形象的多样性”等等。“我所尝试的,是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解读文学作品,用以纾解我们今天的困惑和疑难,也就是说,我想和大家一起向这些作品学习如何理解世界。”

分享会现场
作为“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张莉努力尝试以一种互动的方式重新理解女性文学或者是女性命运。“我有个活力四射的研究生团队,我要说,这本书也得益于和年轻人们的互动,有时候他们会给我提出问题,提出他们的困惑,我对年轻人的解答也体现在这本书里。”
《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不是高深的课程,张莉谈及,更希望这本书是一种美好的陪伴,是读者随时在地铁、咖啡馆,或者美甲店里可以翻开的一本书,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地阅读,它适合碎片时间阅读。“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在未来某一个特殊的时刻,想到这本书里我讲到过的某位妻子、某位母亲、某位女青年、某位中年女性,如果她们的故事能让你在某一刻不胆怯、不孤独,能有同伴或者同路之感就再好不过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对镜’。‘对镜’在古代的意思是‘对镜贴花黄’,但在我这本书里,是‘以她为镜’。有时候她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可以向她学习;有时候她做得没那么好,我们可以从她具体的处境里面反观自身。”张莉说。

《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
书的标题中使用了“对镜”这一意象,而为什么对镜一定是女人?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对着镜子观看自己?嘉宾们认为,在过去很漫长的时间里,女性由于社会空间太小,只能待在家庭和房间里,能看到的风景只有镜中的自己。
“所有女性画家的作品都是对镜的自画像,因为她没有别的模特,没有广阔的空间去征服、去占有,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多么有价值,只能回到内室对着一面镜子看看自己。”作家柏邦妮说:“在女性形象和女性故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这好像就是女性的特点,我们一定会回到自身去思考这个问题。男性是向外的,扩张型的、征服型的;相对的,女性是趋内的,回到自我问自己应该怎么样。所以‘对镜’这个词打动了我。这个意象本身既简单但又很有穿透力。我特别喜欢张莉老师这本书叫‘对镜’。”
“我觉得女性评论家和男性视角有很大不同,男性的很多思维写作还是理性的产物,是大脑的产物,他会去布局、谋篇、思想意识、思想境界。但是女性天生有一种很强的共情感,她会去想这个人的生活处境,她在里面有多难,她有多么疼痛。”柏邦妮说。
作家水木丁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她经常会被认为比较像男作家,“其实女性的语言跟男性的语言不太一样,女性的语言非常善于用比喻句,非常会修饰。比如张爱玲的语言就是非常漂亮的女性语言。我大学的时候看海明威‘八分之一的冰山创作原则’,当时觉得那是必须要遵守的。后来等我慢慢写成熟以后,发现海明威也变成了我们后面所有作家的牢笼——必须去遵守的八分之一理论,成了我们的束缚。尽管我知道它还有很多优点,可是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到达不了,因为非常简洁的说话方式,那是男人天生的语感。”
《对镜》中,分析了22部作品。水木丁更关注其中的王安忆小说《我爱比尔》,她说:“小说女主角是一个文艺青年,她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她既不是完美的女主角,也不是完美受害者。她有虚荣心,有私心,但她没有害人之心,但是却慢慢走到了很不好的境地。我对她充满了同情,同情她迷失自我的状态。”
《对镜》里《我爱比尔》这一讲提出的问题是“女性在爱情中如何成为自己”——爱情里的女性,是隐藏本真的自己,成为别人喜欢的人,还是成为本来的自我呢?“在《我爱比尔》里,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爱情是成为自己,永远获得不了的爱情其实是因为永远没有成为自己。”这是《对镜》给出的答案。
评论家、《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认为,从我们上语文课开始,在小学、中学,甚至到了大学专业学习阶段,很少注意过把那些女性写作者作为一面镜子,去对照发现自己的语言方式。在漫长的语文教学阶段,并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女孩子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是女性的文字。在我们的语文教材或者语文教学的传统里面,并没有那么多性别之分,或者很少意识到主流文学语言的男性特质。我觉得今天应该做的,除了寻找文学史上的父亲,我们还应该找到自己文学写作的母亲,找到自己语言的方式,自己的腔调。
“现在网络上的声音,让我感觉到这个时代有许多人对于情感方式的理解,抱着刻板的、一丝一毫不能逾矩的态度。其实在《对镜》这本书里面,一直重复一个常识:女性这个群体包含着巨大的差异,关于阶层的,关于地域的,关于时空的差异。当从这样包容的视角,再去理解婚姻,理解爱情,理解人类最美好、最微妙、最多维的情感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张莉提出,只有当普通的女性拿起笔,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才会闪耀。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什么?张莉认为:“我当然希望这个时代出现萧红,出现丁玲,但更希望普通的女性拿起笔写下自己的际遇,哪怕它的文学性没有那么高,哪怕这位一辈子只写这一部作品。真正的女性文学作品会让更多女性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在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提出了‘人的文学’的概念,关注‘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这个‘引车卖浆者流’其实就是普通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传统——关注和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鲁迅先生的《祝福》,书写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祥林嫂的一生,这是他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同时,我们的优秀传统也包括让那些最普通的民众拿起笔书写自己的生活。我想说的是,当最普通的女性拿起笔写自己,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才会闪耀。”张莉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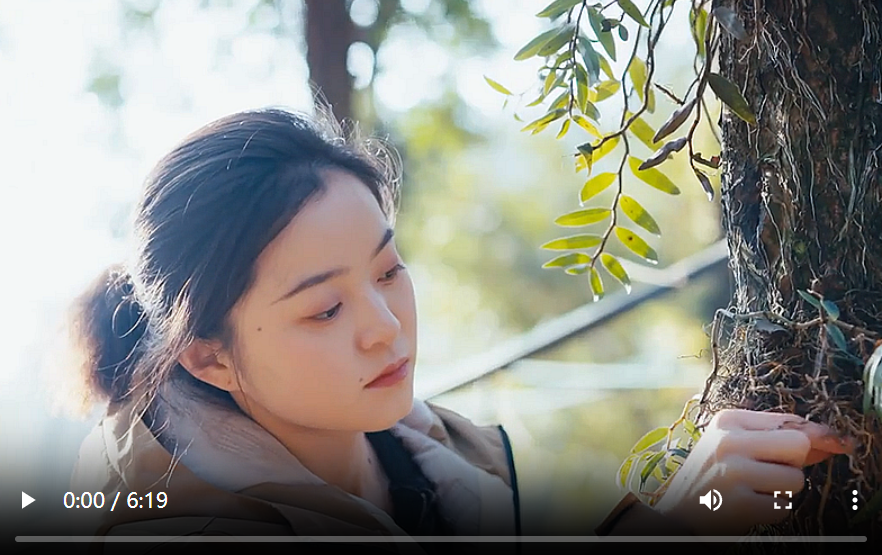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