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导演戴墨:感动因人物自然发生
由陈思诚监制,戴墨导演,张冀编剧,演员张译、李晨、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等主演的电影《三大队》正在热映中。影片自上映以来已收获4.5亿票房,豆瓣评分高达7.9分。
电影改编自网易人间工作室深蓝的非虚构报告文学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罪与罚的故事,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张译 饰)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他出狱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踪在逃嫌犯……而漫漫执着的追凶路途,并非简单地歌颂英雄,而是展现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编剧张冀最大的改动,是让现实中孤独的追凶路,变成了一支理想主义队伍热血的征途,虽然这场征途只是半程。而这个基于虚构的改动,也恰恰从更普世的视角为影片平添了另一份真实。观众通过共情每个普通人没能做到的坚持,从而更懂得了程兵为常人所不能的执着和这份精神的宝贵。
要演绎一群默契老伙计的故事,监制陈思诚找来了自己多年老友。张译、李晨与陈思诚自《士兵突击》结下深厚感情,之后也都参演陈思诚转型导演的《北京爱情故事》。导演戴墨则是自《北爱》开始与上述诸位结缘。当时他初入行,中戏毕业演过些话剧,第一次见识到剧组的规模看啥都新鲜又稀奇。他在剧中演配角也做副导演,之后一路在陈思诚团队中学习成长,执导了《唐人街探案》网剧中《玫瑰的名字》篇章,电影《误杀2》等影视作品。陈思诚将电影《三大队》的剧本给到戴墨之前,他刚刚拍完了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剧集《球状闪电》。
看完剧本,原版计划休假的戴墨立刻订了机票飞回北京和团队开会,他至今记得对这个故事拿起就放不下的那份心情,“舍不得错过这个剧本,否则我一定会后悔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作品。”
对于犯罪题材,身在陈思诚团队的戴墨早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电影《三大队》是一次不同的尝试,摒弃了他们擅长的悬念渲染与煽情反转。冷静克制的现实主义画风出现在“陈思诚监制”的电影里,这很罕见。
影片上映期间,导演戴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一段“去英雄化”传奇的改编中,依然有真实、震撼人心的力量。

导演戴墨
【对话】
三大队其他队员是程兵的镜子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机缘下接到的这个项目。这个故事最初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戴墨: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去年,我刚刚拍完《球状闪电》从横店回到杭州,那个项目在横店拍了4个月,当时觉得很累很辛苦,本想着要去云南度个假,结果就收到监制给我发来这个本子。看完这个剧本以后,我立马就订票回北京了。
真是觉得非常喜欢,首先是这是一个很好看很成熟的剧本。同时我自己也好奇,程兵这个人真的存在吗,是编剧塑造得太好了吗?然后我又看到了深蓝老师那篇文章,了解到是取材自一线刑警的真实故事,由衷地对这个故事和这群人产生了敬佩之情。
你知道在中国14亿人口这么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大海捞针,通过自己做各种职业,去摸排去调查,去找一个人,太难了。而且他决定要去找王二勇的时候,他可没想说这是12年后能完成的事儿。人知道一件事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份期许,但其实没有时间期限,所以他真的是下了决心,要付出一生的代价去完成这一件事情。
这东西太好了,我舍不得错过,错过的话,我觉得我就是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了。
澎湃新闻:和之前的作品经验相比,不同的改编来源,创作方法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吗?
戴墨:我第一部电影《误杀2》是一个纯类型片,很多时候你要去营造一种类型片的气氛,包括在拍摄手法和很多场景选择和戏剧的情节上,要把它弄得比较极致,让人看着可能刺激一点。
后来拍剧集《球状闪电》是一个大的科幻类的题材,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着力去建立一个世界观的东西。每个戏工作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
电影《三大队》是基于纪实文学改编,有真实的底色,一开始我们监制、编剧等主创一块开会的时候,也讨论过到底是要更偏向类型片,还是用更加写实主义的风格去完成。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写实一点的风格,更适合这样的一个题材和故事,能够把更多的人物内心的东西和遭遇的事情,用一种半纪录式的、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让观众代入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的摄影指导董劲松,是比较擅长纪实风格以及肩扛摄影,摄影机很贴近演员的方式,也是我们团队的第一次尝试。

《三大队》剧照
澎湃新闻:对比原作的那篇文章,电影里三大队队员做的各种工作,其实都是程兵一个人做的,对其他人的构思和设计,是否也是从程兵的经历出发找灵感?
戴墨:冀哥(编剧张冀)对这个事情做的最大的改动,就是他一个人的追凶,变成了三大队一个队伍的事。这样的调整,最重要的是将个人的英雄化色彩给减弱了,这种去英雄化的表达,更增加了一种真实感。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像程兵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家身边可能没那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我们了解到很多警察,他们也是默默无闻地在保护着人民的安全。
至于大家的分工,确实是按文章里所写的程兵做的职业给合理分配了,让大家一起去寻找王二勇。所有这些职业设置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要跟更多的人去接触。比如夜宵摊、环卫工、网吧收银等,都是因为人流量大,他去小区看门的原因也是因为能看人,去开出租车的原因也是,这是他们的终极行动线,要在人群当中寻找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丢掉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好像除了程兵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现实主义,而电影里,放弃和坚持一样都是难的,是深刻和值得尊重的,怎么设计和刻画每一次的放弃?
戴墨:我们把一个人变成一群人,从功能上说,好像是群戏能显得比一个人的寻找来得更加丰富一些,会产生很多的兄弟之间的戏的化学作用,一个人如果要是追的话,可能会让这个片子变得枯燥。
但后来我们也渐渐发现,可能每个人的离别也更加反作用于程兵这个人。比如小徐为了爱情,或者比如蔡彬为了自己的身体,马振坤为了自己的家庭,廖健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人,人在生活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难以舍弃的东西。我们没法苛责他们,这些理由恰恰能够更具体地说明程兵的处境,告诉观众,程兵到底为他的执着放弃了什么。
如果说每个人代表一样东西的话,小徐的离开是让观众意识到,程兵在追凶的路上,他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蔡彬代表的是健康,他停下而程兵没停下的时候,其实是程兵放弃了自己的健康,另外他放弃了他的家,他的孩子,放弃了赚钱的机会……三大队的其他成员是他的镜子。
那一刻,没有机器、没有灯光,他们就是“三大队”
澎湃新闻:《三大队》集结了很优秀的演员班底,大家都是很会演戏的演员,作为导演的工作是不是就非常省心?
戴墨:当然是更省心,因为这帮演员都太好了,而且他们在一起都互相合作过,这就造成了一种不用明说的默契,加上大家都很专业、很敬业,又都非常适合各自的角色,所以就不用怎么刻意去“塑造”。 我们第一天的第一场戏,就是夜宵摊从案发现场出来,三大队跟二大队有一个“过招”,就简单几句话,人物关系全明白了,这是新来的,这俩是烟友的关系,有人是插科打诨的,有老师父把新手保护起来,一下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很明确地建立起来。
我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处理群戏的关系,比如首先得把位置定好,比如说程兵坐这儿,师傅要坐他旁边,马振坤跟廖建要在一块坐着,蔡彬跟小徐在一块坐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坐法,不是别的坐法?这种戏跟戏的人物关系,是为戏剧效果服务的。从那个座位关系里就能看出,老蔡一直在保护着小徐,廖健和马振坤是会欺负小徐的,觉得他刚刚毕业,学的全是书本里的东西。
澎湃新闻:唱歌那场戏超感动,当时拍的时候拍了几次,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戴墨:这场戏是重场戏,本来想多拍两次的,但是拍不了。已经杀青的李晨,知道有这么一场重场戏,坚持要晚走一天。当时戏里边有一桌,他们在喝酒,戏外边我们也摆上一桌,给他们预热助兴。
那天先是我和陈思诚监制、晨哥预热先喝上了,喝着、聊着培养感情,差不多到那意思了,我说“走!进场。”结果拍了一条之后,戏里边的喝酒劲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一开始还是大家说“多来点,找找感觉”,到后来得劝着说“少来点,不行了”。
那是不可复制的一场戏,好多都是现挂的即兴的表演,比如马振坤突然起身,气势汹汹地去亲了媳妇一口,其他人在外面瞠目结舌地竖起大拇哥。这种特别鲜活的表演,我们最后剪辑的时候都给保留下来了。
哥几个这些群戏,每次看我每次都很感动,有一些时刻,你会感觉到他们是跟三大队合二为一了,它很微妙,没法去解释,这东西挺神奇、很玄学。
唱歌的那一刻,我在现场,就相信那是三大队突然间从平行时空穿越到这来了,他们这几个人就长成这样,遇到了这个事情,在这吃饭喝酒聊天。
没有机器,没有灯光,没有什么拍戏、表演,他们不是演员,不是张译、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不是,他们就是程兵、蔡彬、马振坤、廖健、小徐,那一刻,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就是合二为一了。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教育背景,早年做演员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观念和在现场的工作习惯?
戴墨:我是中戏毕业,毕业之后就做了几年的话剧演员,话剧舞台上那些年,我觉得对我现在做导演还挺有帮助的。虽然那会儿也是演员,但我们都是在跟导演同时在排练场一起工作,也会感到自己有非常多的创作欲望,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学到非常多调度安排的技法。
像我的第一部电影《误杀2》,它是一个比较单一场景的事件,其实有点像戏剧,外面有一群围观的群众,里面是一个劫持现场,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封闭空间的时候,怎么样去排演调度,又得有一个规定情境中,让人感到时刻会有危险。那种处理大的规定情境,并在其中在现场去排这个调度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是我从话剧和中戏的学习中积累下来的。
这次电影《三大队》,比较多的群戏,因为这次我们想追求一种真实的感觉,所以很多戏都是在真实的场景里拍摄,这带来一个问题是,拍摄的空间会很小,比如我们第一场案发现场家里,要塞很多警察,加上尸体摆放的空间之后,甚至都没地方给摄影机和灯光下脚的地方了。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里,安排演员的表演走位,让大家同时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我觉得跟我多年话剧舞台的经验有关系。
追凶的过程,也是追寻自我
澎湃新闻:看到你在一个采访里提到有注意“不要自我感动”,但原本故事就是很容易感动,拍摄的时候怎么控制这个度?
戴墨:确实很容易感动,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加入很多手法去渲染感动。我跟译哥交流的时候,也是达成一个共识,先别感动我们自己,而是通过人物,通过戏剧情节和故事推动,让感动自然发生。
整个拍摄都比较克制,镜头选择上是比较冷静,没有去过多的推拉摇移什么的,好像要强调一下某些情绪,或者过多用音乐铺垫渲染,这些都没有。
我们做了很多减法,甚至监制还提过这次完全不要音乐,后来觉得这样实验性太强太大了,虽然我们是想追求写实,但也还是一个商业片,还是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这次整个音乐的量,比我们团队的其他作品里的要少了很多。
但再怎么想克制,有时候到那个点了,情绪还是要让它抒发出来。比如译哥在公园里突然“找不动了”那场戏,他说他不想哭,结果到了现场,他在演的那一刻,剧本里是要发短信给前妻,他突然间觉得他发给前妻可能不太对,想不到发给谁合适,他就在那翻。
道具老师基于程兵应该没什么社交,他的通讯录人也没有很多,他翻着翻着就到头了,然后他还在那一直翻。突然间我发现他情绪有变化了,我就说“镜头赶紧往上上!”我要拍近景,我怕抓不着,就赶紧让摄影师去把他情绪给抓住,就拍到他很崩溃的那一幕。后来他自己还说“怎么突然间这样了”,连他自己也很意外。
澎湃新闻:同时那场戏,你也用声音的处理去解释了他内心的那种波澜,有一个从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也很精彩。
戴墨:对,我想把旁边老百姓的气氛,用声音的一种方式注入到他的世界里。那场戏是他从看守所辨认完嫌疑人之后出来,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那张脸,但出来看到了“破碎”的自己,他开始反问自己,怎么这么多年经历成这样,还把一个无辜的人给害死,我这样真的值得吗?阿哲的死,可能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突然间走到了一个公园,我把那个声音从外界输入到他的耳朵里,突然之间有一个泡泡在他眼前飘了一下,他就顺势看到了旁边。他一下从自己的那个世界打开了,听到大家的欢笑声,跳舞的音乐声,小孩子们玩耍的声音,“生活”这两个字,一下子就输入到他的眼睛当中,让他意识到原来周遭的生活是这样,那我的生活在哪?那一刻,我觉得他应该问自己非常多的问题。我自己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程兵这个人物,以及片中多次提到的“我执”?
戴墨:有一场戏是程兵来到马路上,看到了很多镜子当中的自己,镜子里的镜像有很多面,很多的镜像是破碎的,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他的很多面都碎掉了。在别人看来,他的人生是失败的,婚姻失败了,事业没有了,他跟女儿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唯独在(追凶)这件事上他想要一个成功,所以他就选择了付出12年。
你说他偏执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在追凶的这条路上,丢掉了这么多世俗意义上的东西,他一定也在寻找他自己的自我。他肯定有很多的原因去选择追凶这条路,可以说是为了躺在冰柜里的受害者,也可以说是为了给他茶叶蛋的受害者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师傅、为了三大队的荣誉,为了自己当时许下的承诺,同时他也想寻找到他自己。他在监狱里也一直在重复着问“我是谁”。所以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可能他才真正地能跟自己有一次和解。
我最近看到很多观众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很多都说得特别好。一千个观众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些解读的方向和创作思路不谋而合,这是一种与观众的对话和默契,观众能够懂创作者的表达,对于创作者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用悬疑犯罪类的故事,探讨时代中的人
澎湃新闻:和陈思诚、张译、李晨也都是从《北爱》开始合作,看他们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戴墨:《北京爱情故事》是我参与的第一部电视剧,那个时候刚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剧组都是第一次见。第一次发现,原来拍戏的剧组是那么多人一块工作,我那时候排话剧没那么多人,看灯光轨道什么的都觉得新鲜,看着哥哥们表演,就觉得他们真厉害。那会儿我和他们仨的对手戏都不多,捎带做一些副导演的工作。这些年可能是,“他们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变老”哈哈哈。
译哥这次长出好多白头发,但他一直就是一个对戏极为认真执着的人,到现在他的表演,我觉得已经“出神了”,对于人物的理解特别透彻,这次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拿到一个表演类的非常高水准的奖项。晨哥,我觉得他也是演技更精进了,同时他的酒量也更加精进了。
当然,变化最大的是陈思诚导演,这些年我看着他从演员成为导演,又成为监制,成为电影的投资人,变成一个外界所谓的“产品经理”,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特别大情怀的创作者。很多人看《唐人街探案》系列,觉得是一个纯商业片,是闹腾的合家欢喜剧,其实他一直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藏着一种深刻的,包括“唐探”的时候,每一部电影它前面都有一段话,是和精神思想有关的,好多观众不太注意到它隐藏的东西,其实他是有大情怀的。另外我觉得,他的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当了父亲以后,变得更加成熟和温柔了。
澎湃新闻: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从事这个行当的?又是从演员转向导演?
戴墨:我读中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那会儿老师甚至会给我们这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发一些美容美发或者蓝翔挖掘机这种技术学校的招生简章。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应该去做什么,很迷茫。但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文艺,在班级里组织各种文艺活动,所以后来参加了艺校的招生,发现自己对表演特别有兴趣,就考了中戏。
后来毕业了,做演员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没有长得特别帅,演技也没有特别好,恰巧有机会在陈思诚导演身边学习,他觉得我大学也学过导演,应该要多学习丰富自己。其实我从演员到导演的这个选择,一开始是相对“被动”的,是受了陈思诚导演的“鞭策”,他鼓励我去做副导演,在现场帮忙,又让我去学习剪辑,通过这些训练,进入到导演创作的道路上。
澎湃新闻:你也参与过“唐探”这样更重案情和类型的剧集创作,两部电影也都与犯罪题材有关,好奇这是你本人的兴趣和长处,还是因为刚好结识了陈思诚?
戴墨:我一直都很喜欢悬疑犯罪类的故事,我更想探讨的是人,其实更多的案情案件,有时候背后的那个人挺值得去讨论的,只不过我们通过悬疑类、犯罪类的题材去反映。包括平时生活日常里,社会类、法制类的新闻我都会格外关注,一些新闻事件会反映一个时代里特殊的个体或群体,我会在意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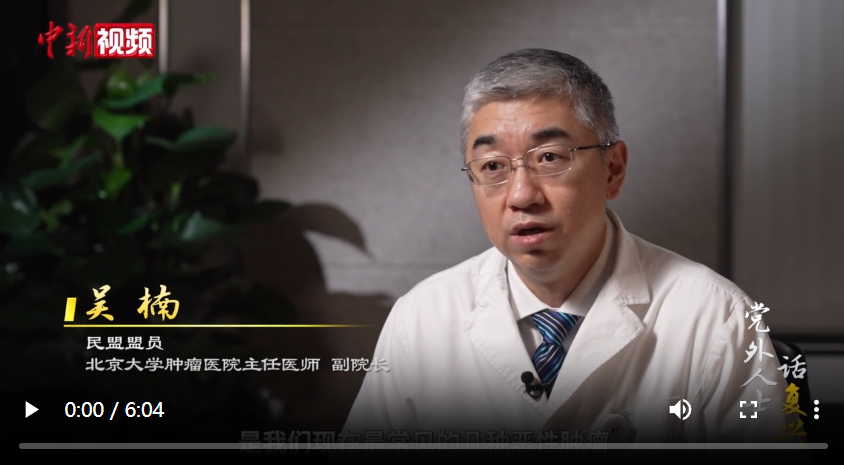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