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王火: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98岁的王火一直保留着一块铭牌,上面镌刻有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23岁时,他与2000位旁观者一起,见证了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的公审,那两年,他奔波于南京的街巷,收集证据,重访故地,在南京寒冷的冬天里,他拜访了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发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重要报道,成为第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
202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距离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5年,“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战八年印象却仍非常深刻。”王火说,那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磨灭的经历。

王火近照。受访者供图
铁证
一群天皇的勇士们搜见了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便要强奸,结果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强硬抗拒,于是强奸未遂,而陈李秀英却被那些“皇军”们的枪尖,戳了三十三刀,奄奄一息地被鼓楼医院的外国籍医师抬入院内,经过诊治,她的伤是好了,但我见到陈李秀英时,她已经是一位脸部比“夜半歌声”上的“宋丹萍”好不了多少的女子。
——摘自王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
98岁的王火耳朵已经没有那么灵光,在电话里,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我已经要100岁了,太老了,耳朵不是很好,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你能把你的问题再说一遍吗?”
但讲起当年采访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经历,他的声音又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当时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性,她为了反抗日本人的欺辱,身上中了几十刀,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王火是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中国记者,那些讲述和报道成为日后证明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重要证据。
写出一系列南京大屠杀报道时,王火只有23岁,李秀英大王火六岁,1947年,李秀英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中出庭作证,王火先后多次采访了她,对王火而言,“记录下李秀英的故事,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
在当时,大多幸存的受害者羞于出头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为抵御敌人,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她是以一位抗日女战士的身份屹立着的,她虽被敌人毁了容,但抗战胜利了,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指控日军暴行的女同胞。”
王火还记得,1947年初,天气极寒,两人的对话从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到玄武区鱼市街卫巷李秀英的家中,讲到血腥恐怖处,“她落泪,我的心战栗,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2005年,王火在得知李秀英逝世后,撰写了悼念她的文章《宁死不屈的“圣女”》,其中还原了当年的经过。
“12月13 日下午,当时十九岁的李秀英婚后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躲在南京国际难民区内一个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9点,来了六个日本兵,他们抓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来准备奸污,又要来抓李秀英。李秀英想:我宁死也不能受侮辱,她咬着牙一头撞向墙壁,顿时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日本兵只得丢下她走了。
“中午时分,突然又来了三个日本兵,赶走了躲在地下室里的男性,一个鬼子上来要强暴李秀英,她一把就夺住这鬼子兵的军刀柄,同鬼子揪打起来,她咬鬼子的手,卡鬼子的脖子,扭成一团,同鬼子兵在地上翻滚,其他两个鬼子兵跑过来帮忙,用刺刀乱戳她,她脸上、腿上、背上都刺伤了,最后,见她顽强,一个鬼子一刺刀狠狠戳在她肚子上,她终于松开双手血淋淋地昏死了过去。”

1937年12月,李秀英被送入南京鼓楼医院救治。受访者供图
李秀英告诉王火,没有人能想到她挨了37刀,昏迷7天后,还能活下来。
许多年过去,王火仍记得当时采访李秀英时她的模样:语气坚强,神情严肃。但面部受损,日本兵用刀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脸面都割损了。“当时天气冷,她总是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着头遮着脸,我不忍心凝视她或多去看她的伤痕,我觉得那会是对她的一种不敬。”
王火记得,他后来见到了登在报纸上的李秀英的照片,她脸上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消磨逐渐平复了,尽管这样,仍能看见曾经的痕迹。王火还发现,几十年来,他看到李秀英在报刊、电视上的形象,都是没有笑容的。
以笔为戎
日本军队在难民区内屠杀百姓,看见了他(梁廷芳)就给了他一刺刀……同时他的伤口也被摄入电影,这次他随秦德纯次长去东京作证,放映给战犯者的电影上就有他,这一位道道地地的证人,在东京法庭上,曾经慷慨激昂地发过言,据说日本的战犯们曾经都颤颤地低下了头。
——摘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如东县。六岁时,他随父亲迁往南京。在此地生活多年,年近百岁的王火仍然记得,童年时曾跑过的南京街巷,父亲也曾经带着他去过雨花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火,王火跟随家人辗转安徽、湖北、香港,最终又回到上海。
在回忆录《九十回眸》中,王火写下,时为中学生的他,曾冒险游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慰问孤军奋战的八百勇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过抗日传单。
1942年7月初,18岁的王火由上海到南京转道安徽去大后方,南京城的情景与抗战爆发前他在南京居住时完全不同,“在南京停留时,只见人迹稀少,断垣残壁,下关江边一带本来热闹繁华的地方尽皆没有了。”此后,他又步行至河南洛阳,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
这年,王火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一路上,因战乱和饥荒,王火目睹了灾民们饥饿漂流的可怜景象,在晚年的回忆录里,王火将在这段颠沛旅程中看到的场景称为“人间炼狱”。
王火的新闻生涯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事故,1943年夏天,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学生中毒事件,王火参与了抢救同学的工作,亲眼目睹了某些医生不给穷学生好好抢救的行为,他撰写了一封批评稿投给《江津日报》,很快被刊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觉得为人民做口舌还是好,可以为老百姓讲话。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学新闻当记者的心愿。”
次年,王火北上投考复旦大学新闻系,鼎鼎有名的陈望道、萧乾成为了他的老师。读书时,王火参加过陈望道掌舵的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也上过萧乾的“英文新闻写作”课,他说,赵敏恒的“时事研究”课上得像新闻发布会,储安平在“报刊评论写作”课上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大招牌教授很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时,王火就受聘同时担任三家报刊杂志的记者: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和台湾省报《新生报》的驻上海、南京特派员。
194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研石教授给了王火一份工作——以驻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自此,王火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持续两年的追踪报道,成为了当时第一批揭露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之一。
1946年,王火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见到谷寿夫,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谷寿夫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纵兵肆虐,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等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迂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
次年2月,王火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谷寿夫的公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据统计,旁听人数约2000人左右”,王火在为《时事新报》撰写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公审中,检察官起立宣读了长达4000余字的起诉书,并补充道,“略谓京市大屠杀,历时数月,区域包括城郊城内,被害者数十万人”,尽管有幸存者和纪录片为证,谷寿夫仍然强调他不应为南京大屠杀负责。王火见证了公审时的群情激愤,“四周嚷嚷愤慨之声不绝”。
3月10日,谷寿夫宣判,被处死刑,判决书中认定,“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庵、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
妙手著文章
抗日战争中,仅仅一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中国军民就被杀了三十万,大大超过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的灾难。我们能不如实地写出当年的实情使中日现代的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了解真相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了解历史才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摘自《战争和人》创作手记
1949年,王火获得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原本想要向自己的老师萧乾一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1949年后,王火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后来又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参与了《中国工人》筹办,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在山东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
1944年起,王火就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小说,“很多素材在我头脑里,想要喷薄而出地爆发一样。”王火下决心要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才有了后来的《战争和人》。
20世纪60年代初,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这是《战争和人》的前身。不料,所有书稿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70年代末,王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在出版社的鼓励下,他决定重新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她下了决心,一咬牙,自己用右手的食指猛地插入右眼,她哼了一声,立刻将右眼珠血淋淋地挖了出来,顿时血流满面了。绝不能忍受日本鬼子的侮辱!她宁可瞎!宁可死!她那满面是血的右眼眶变成一个血窟窿,样子一定是非常怕人的。”
由于印象深刻,王火在《战争和人》三部曲中写到庄嫂在南京大屠杀中惊心动魄的遭遇,基本是通过当年对李秀英采访获得的印象写成的。王火曾说自己的写作标准:“写一个真的、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不是我见过的、不了解的我不写。如果我用真名字写的人和事,那都是真的。我写南京、上海,人家就说我写得真像,因为我在这些地方生活过。”
重写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1985年,在完成第一部的稿件后,为了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王火的头部撞到一根钢管,左眼视网膜受了伤。后来又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终至失明。
王火只能凭借一只眼睛写作、生活。看东西不准确,有时倒开水容易倒手上,夹菜容易夹到碗外面去。写稿的时候,他需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一只手拿笔,另外一只手拿着个放大镜,然后用手压住纸写,字迹有的时候就像“画符”一样,“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写了,因为抗日战争对我来说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磨灭的经历。”
1993年,这部共167万字,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的长篇巨作终于完成,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愿我全力以赴写出的书里的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历史必由之路……能可信地给人以感染,使人看到苦难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惨历史,懂得现在,知道未来,明白自己的责任!”王火在《战争和人》的后记中写道。
南京大屠杀与我
署身于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南京,看着龙蟠虎踞的日下形胜,这种锥心泣血的感受总是随着血淋淋的记忆,不断强烈侵袭着我。我不能不想起 1937 年 12 月日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高潮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周之久。当时全市被烧毁的房屋约三分之一,无辜同胞惨遭杀害达 30 万人以上。只要想起这些,我心情总是变得非常压抑、非常愤激。旅游的欢愉兴致也就受到了挫伤。于是,从我下榻的金都大酒店九楼的窗口,外眺南京四下里云霞斑斓、茫茫无边的景色时,我常默默凝思,怅然不悦,沉浸在苦涩复杂的心情中。
——摘自王火随笔《血色回忆》
晚年的王火,深居简出。他住在一间并不大的屋子里,书籍散落各处。女儿王凌说,父亲已经不大写作,但几乎每时每刻都“拿着那柄加了小灯的放大镜”读书。前年,王火经历了一场重病,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虽然已经年近百岁,但王火还腿脚利落,能一个人爬楼梯到二楼的家中。
他不能吃猪肉,每天要吃蔬菜,吃萝卜、冬瓜,白水煮,不放油。大部分时候,清晨八点起床,晚间,他在音乐声中入眠。
晚年的事情王火已经不大能记得清了,前些年,王火在接受采访时说,“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战八年印象却仍非常深刻。听到许多事,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写了,因为抗日战争对我来说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磨灭的经历。”
田闻一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与王火共事过,他还记得,多年前,两人聊起过对《战争和人》的看法,“王老特别谦和儒雅,即便面对的是我这样的晚辈,他也会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我,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王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的书不是写给老头子看的”。王凌还记得王火有次看到一部“抗战神剧”,非常恼火。他嘀咕说,打仗真有这么容易吗?怎么可能两个飞镖就把日本人打死?太不靠谱了!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历史。
王火谢绝了大部分的访客,但如果要谈起过去的那段历史,即使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他也仍然能够侃侃而谈。2022年夏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几经周折,联系到王火,在电话中,即使很多问题要大声地说上三四遍,但王火思路清晰,将他当年在南京采访的经历、后来写作抗战类小说的经历娓娓道来。
2022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纪念馆推出“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系列人物访谈,王火作为第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被选入内,系列中的其他人,或祖辈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历史,或创作过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作品,或为南京大屠杀历史国际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但又是极不普通的一群‘有故事的人’。我们想听他们讲述他们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想从细节中找到那个我们需要一代代传承、铭记的理由,那个内心不能被抹去的点,那个一触碰可能就会瞬间流泪的最柔软的情感,也是最坚韧不催、不容被侵犯的地方。” 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纪念馆在国家公祭前夕派出采访组,到街头巷尾采访普通市民,问他们,“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许多人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纪念馆工作人员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它是对侵略与主权的思考,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普通人来说,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让我们直视历史,让我们不敢忘、不能忘,让我们每个人思考,如何做,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不让历史重演,让我们过上国泰民安的好日子。”
当问王火,他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自己已经活了快100年了,没有什么心愿了。但谈及南京大屠杀,他又说,是不是应该把写的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集结成书,“想起过去在南京采访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李冰洁)
参考资料:
《王火文集第八卷:失去了的黄金时代 风云花絮 启示录》
《王火文集第十卷:九十回眸》
《王火散文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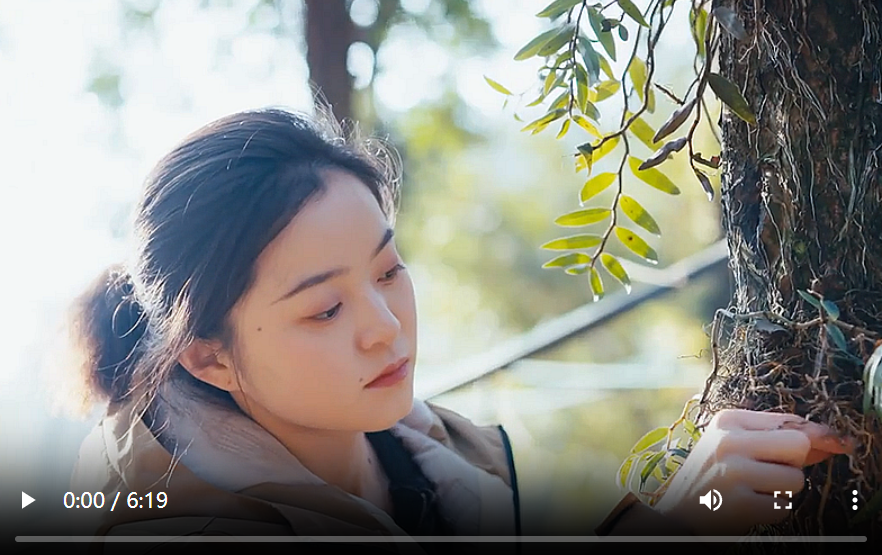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3998号